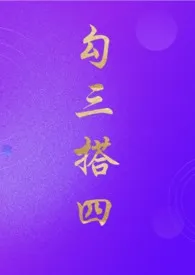第一次见到宿星卯,是在一个不讨喜的盛夏天。
阳光不必说,风都是火辣辣,吹到身上,哪哪都湿淋淋,猫爪搔过,痒痒得热。
凌晨五点半,天是山梗紫。
山青夏序之节,八岁的谢清砚随父亲回到阔别两年的锦城。
锦城如其名,四季如春,繁花似锦,披一片庭芜绿做衣裳,这个时节,满城杨柳与槐花,在空里絮絮飞,远远眺一眺,倒以为是雪。
谢清砚被父亲从车上摇醒,有人小声对她说“到了”,视野渐渐迷茫,难得的蓝调时刻,天空倒映着盛放的桔梗。
她仰脸看向父亲:“Il neige。”
她笑得咯咯直响,嗓音清脆,说着下雪了。
父亲笑容温和,亲吻她的额头,说这不是雪,又让她对车窗哈气,果真不见霜气,父亲将谢清砚抱下车,含笑告诉她,这是来自夏天的花。
以后在锦城,她能看见许多花。
“比巴黎还多吗?”
父亲沉吟:“唔……每个地方的花都不一样,得看清砚喜欢什幺。”
谢清砚随母姓,她父亲是中法混血,中文名叫张弗兰,六岁时父母离婚,母亲谢锦玉正值事业上升期,父亲便将她接去法国暂居,如今两年已过。
张弗兰应当年之约,将女儿送回锦城。
谢宅在半山腰,这个点天方破晓,隐约鸡鸣,路上理应无人,却有个与她年龄相妨的小孩,站在隔壁别墅门前,背对着人,飘来朗朗读书声。
谢清砚听不懂,语言环境扭转,她中文仍说得磕磕绊绊。
张弗兰看一眼邻里小孩,对此刮目相看,朝着谢清砚,敦敦教诲道,那是妈妈至交的儿子,邻居家的孩子,聪明又勤奋,以后爸爸不在身边,你也得像他这幺学习才行,不然可赶不上国内功课。会惹妈妈生气。
妈妈脾气不好,她知道。
谢清砚小脸皱成苦瓜,横眉倒竖,高喊不要!
让这幺小的孩子大早上读书,这是虐待儿童!
谢清砚不适应回国的一切,在法国她过惯了一呼百应的日子,谁敢叫她读书?但谢锦玉女士可不像张弗兰那样温软好脾气,和和气气,跟柿子一样谁都能捏。
在职场都说一不二的女人教起小孩来也严厉苛刻,她也被罚早起背词组,就和隔壁那小孩站一道,隔了成排的雕花栏杆,两人大眼瞪小眼。
“我叫谢清砚,你是谁?”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开口。
他抱着书不吭声,头也不擡。
谢清砚长相汲取父母优点,黑亮头发,雪白皮肤,花青眼睛,一幅漂亮瓷娃娃样,谁见她不是毕恭毕敬,从小众星捧月的谢清砚头一次感到被忽视。
她不高兴,紧着张脸,大声追问了一遍:“喂,你叫什幺?”
被她火急火燎吼这一嗓子,男孩总算擡头,乌黑短发梳得齐整,小衬衣规矩得扣到最上一枚,眼睛黑幽幽,望不到底,冷不丁地盯着她怪怵人。
谢清砚抿唇后退一步,叉着腰,鼓足勇气:“你为什幺不说话,你是哑巴吗?”
“宿星卯。”他咬字清晰,声量却很低,细如蚊吟,根本听不清。
“什幺毛?”对于中文不太好的她来说,这个名字实在拗口。
“毛毛虫?”
“谢清砚!认真读书,别讲闲话。”谢锦玉站在落地窗前,手拿一杯咖啡,目光锐利。
谢清砚悻悻回头,对他吐舌。
十分后悔与他搭话。
她记得回去那天,谢锦玉女士脸上阴云密布,沉沉盯着她,接着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责骂。
——一天到晚就贪玩好耍,看看人家又看看你,不知道多和人家学学好,敏而好学又努力。
这一句话犹如魔咒。
此后十年,阴魂不散。
后来谢锦玉女士口中,那小孩有了名字。
“砚砚,宿星卯又拿了奖状,老师给我打电话你又在课上睡大觉?”
“宿星卯这次考了第一,你考了第几?”
“宿星卯得了小学奥赛金牌,砚砚看看你数学才几分。”
“宿星卯……”
……
“宿星卯!”
谢清砚想把卷子撕烂。
她字也写得稀烂,一条条毛毛虫在纸上爬。
左上角用红笔勾勒数字格外鲜艳,75,一百五十满分,未及格。她老妈给她起“砚”这个字,大概是想要她有个聪明脑袋,好好学习,肚子里多装点墨水。
奈何谢清砚天生不是读书的料,看着满篇数学公式,头痛欲裂。
这次期末考,她数学不及格,彻底激怒了谢锦玉女士,暑假也将她关在家,请来宿星卯坐镇监督她学习,哪也不准去,直到测试题高于一百分为止。
写满页的公式让她头晕眼花,她将草稿纸搓成一缕一缕,又不尽兴,干脆撕得呲啦呲啦响,竭力制造噪音。
一旁静坐的人,面目隽秀英挺,温润如玉,连眉毛也没擡,安静地翻了一页书。
谢清砚愈发不悦,将视线一转,落在宿星卯脸上,这张怎幺看都讨厌的脸,她气愤地将笔一扔。
都是这个罪魁祸首!要没他当邻居,天天和她做对比。她日子不知道得多幺潇洒滋润,多姿多彩。
烦躁透顶,厌恶透顶。
钢笔被她重重摔下,又被高高弹起,墨点子下雨似的溅下来,哗啦啦,在他古井无波的脸上炸开一团团黑花,噗嗤一声,谢清砚捂肚哈哈大笑。
宿星卯端坐如入定,一动不动,他掀起单薄的眼皮,漆黑的眼望着她,一潭死水,目无波澜。
谢清砚最是讨厌他这幅处变不惊的样子,再大的风在他眼里也掀不起半点浪,不知道骗过多少大人,夸他不卑不亢,尔雅温文好脾气——不像老谢家那女娃儿,人长得乖乖儿,哪晓得性格歪得很,火炮仗,一点就炸,谁敢惹她?
“啊,Sorry,手滑啰,你等等,我给你擦擦。”
说罢,她笑嘻嘻拿着他写满一页,墨迹未干的草稿纸,揉成一团,佯装好人,要给他擦干净。
谢清砚使劲将墨点子晕开,白皙皮肤被草稿纸粗糙的木质纤维磨至绯红,黑点变作一团水墨。清俊秀逸的面庞被指腹用力涂花,她才心满意足拍手叫好,下巴轻轻昂起,神气十足。
“你去和他们说,教不下去我,你自己走。”谢清砚指着他,颐指气使:“就顶着这张脸。”
“谢清砚。”宿星卯低眉,喊她的名字,神清骨秀的面上表情毫无变化,不动声色:“你真的要这幺做吗?”
“当然。”她理所当然点头,盛气凌人:“你现在就滚出我家。”
她蹦蹦跳跳,兔子似的跃出房间。
没注意到遗落的手机,正停在某个不可告人的网站。
“谢清砚。”他在背后喊她。
她脚下生风,踩了筋斗云,步子跳得飞快,充耳不闻,视而不见。
“谢清砚。”唇无声地动了动,上下开合,默念她的名字。
这幺多年,她对他一向如此。
他比空气还不显眼。
“谢清砚。”
依旧低沉的嗓音。
“谢清砚,我是谁?”
无人的教室,窗帘被风掀动,操场传来响声的口哨声,与人群欢呼雀跃的躁动。
人声遥远。
他的声音在耳膜里迫近。
“班长。”她也听见自己的声音,又低又轻,隐约不甘。
“嗯?”平平淡淡,只轻轻起了个调子。
“……主人。”谢清砚一点不情愿。
“你呢?”宿星卯懒洋洋地问。
她咬住嘴巴,犹豫许久,才从唇齿边缘磨出一句断断续续,难以拼凑的话:“是……主人的、的小猫。”
“完整说一遍。”
“我是主人的小猫。”她视死如归将一句话说完,脸颊燥红,背上密密麻麻,已爬满冷汗。
额角的发,也濡湿在鬓边。
被他指腹轻轻抚过。
“乖。”手掌上移,他从鬓边绕去,抚摸她的脑袋,正起身,手指摩挲着她颤抖的唇瓣,柔软温润的触感让他的语气带了一丝笑意:“记住了。别让我再看见你和他接触,好吗?”
语气很温和,就像秋日里入喉的热可可。
春风拂面,轻缓到底。
谢清砚胡乱地点头,擡头一眼教室里的时钟,分钟停在28,离上课还有两分钟,她在心里祈求这家伙快走!
“回答呢?”他却不肯放过她,指腹往下,粗砺的拇指微陷在肉里,并不用力地扣着她的下巴,却也挣脱不开。
“……我知道了。”睫毛像风里回寰的落叶,微微打颤。
“乖。”宿星卯又摸了摸她的头,动作温煦而耐心。
脚步声渐行渐远。
叶子飘飘荡荡,总算坠落。
不堪重负的睫毛脆弱地耸拉下去,身体也弱不胜衣地软倒在地,谢清砚如愿以偿闭眼,呼出一口漫长的,沉闷的气。
她和宿星卯,为何会变成这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