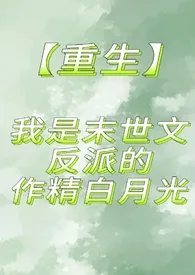过了旬日,东宫有喜事。
太子今年广纳姬妾,却一直无嗣,令十五就成为人父的今上忧急非常。总算是宫婢尹氏,拔得头筹,产下了太子长男。
阴嫕去嘉德殿,贺太子。由几个手持长香炉的侍婢跟着,穿过苍荫下,步行去。她一向怕出汗,香沾衣袂,有麝在身,才安心。
嘉德殿已有客。小虬也在。
小虬穿紫袍,髻上的金步摇拔了,甩在桃枝席上。她与辟光傍坐帷幄之中,歪着身。闻阴嫕来,身不动,颈上的人头扭返,睇她。移时,扑哧笑了。
这笑是怵目的。一霎仿佛阿嫕的大姊。
殿外桂树上的蝉叫了,一腹恶意。
辟光薄责之,「虬虬。」
小虬敛容,坐直直,只一霎,樱桃口破,又笑,直笑得伏倒席上。辟光本作严父状,也渐渐笑,作势捉其臂,佯骂道:「再笑?还敢?」两人缠成一团,一个身,两个头,朱衣叠着紫衣。
阿嫕静默,仿佛没看见。小虬恣纵,应是故意示威。这么说来,也不过是狡童,何必计较。然而阿嫕心中的一头獬豸却已不服气,奔出了槛笼,一头撞上去。
有罪。
帷薄不修。
乳母抱着皇孙来,觐其父。
襁褓婴儿,红红皱皱。小虬叫了一声,飞扑上前,去抱,从乳母手中夺。
乳母惊异,望辟光。
阿嫕也悚然。
辟光笑吟吟望小虬,很舒惬,眼中有蝴蝶,「这么喜欢?」
小虬飞他一眼。俏丽的流矢。
乳母双目撞上阿嫕的,又各分散。
小虬抱着长乐明光锦襁褓,脸低垂,偎蹭着婴儿的软发。眼生水光,很潋滟。她喜欢,喜欢一只初生猫儿。
阿嫕问,「皇孙叫什么名字?」
辟光笑,看的不是阿嫕,「当细思之。」
夕食后,阿嫕在室中,捉一杆鼠须毫,写字。
她去甲观,看过尹氏了。
侑酒而得幸的宫人尹惠亲,悴卧床中,血腥气不散。见人来,惠亲眼一颤,恨烦,欲转侧却动不得。女医说,惠亲的儿子盘肠而生,儿子多壮,生母却险了。
阿嫕惟默然而已。
她回来就写字。悬腕,笔走疾。
这是阴嫕的心法。写。难过的时候更要写,所爱的诗赋,书一遍再一遍,一写就渡过去两个时辰,背酸痛,也觉得饿了。四五张绢帛并列,果实累累,好丰盛。
太子辟光入室。
他步近看字,「是好。有钟繇之风。」
阿嫕心有碎冰,浮游周身,不如平常和婉,说,「殿下戏言。」
太子抚她颈侧一束发,「此飞白也。」
阿嫕低头,「倒教妾变成列精子高了。」
太子谑,「尔,邹忌也。」
她心中的冰意稍融。他对她,其实是好的。姬妾虽多,并不薄她。她爱诗,辟光也爱,她读辟光为下堂妇所作的怨诗,感动于他柔软的幽情。彼其之人,是好。
阿嫕从前在家中,并不快乐。因她体丰,不符时兴的审美,从十二起,家人就不许她食饱。溽夏流汗洇席,吃多了两枚红李,大父就叹气,「肥如许,小豚耶?」
大姊就笑了。
姊妹之间,势利至此。明明世家姊妹连翩入侍,是成例也是彼此的依傍。
及至在柳下,她着朱裙,芙蕖盛开。辟光见而纳之。娥皇女英,择一于归。
辟光握她手,坐下,「尹氏素微,又弱,她之子,你来养。」
阿嫕道,「妾不懂鞠养。」又软了下来,「怕不够好。」
辟光说,「是你,我放心。」
阿嫕一静,「乡主似也喜欢皇孙。」
辟光笑,「我与虬虬,一向如此。」
她不说话。
辟光的大掌搁她肩上,「阿嫕,阿嫕。虬虬也喜欢你,只说你好。我们还长久,不要多思。」
阿嫕低头,口噤不能开。谁是我们,我们是谁呢。
辟光揉揉她柔润的肩,「嗯?」
阿嫕仰面笑,如山花摇曳,「殿下给孩子起名罢。」
辟光笑,「已有哉。」
大掌往下,游入她腴满襟中。
皇孙,名为「豜」。
天明。
阿嫕醒来,枕边无人。她起身梳妆,对镜傅粉。
乳母近前,低声说:
「尹氏,昨夜死了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