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花泽宅邸的下人眼中,关于“老爷”与“明日子夫人”的种种,与其说是明确的画面,不如说是碎片化的声响、气味、光影晃动和被刻意模糊的肢体片段——如同一场在浓雾中演出的禁忌戏剧,只能捕捉到那些穿透雾霭的、令人心惊肉跳的痕迹。
晨光熹微。老管事如往常般最早巡视庭院。当他经过西翼主卧窗外那片精心养护的青苔地时,脚步微顿。
湿漉漉、半透明的薄棉内衬小褂,被揉皱成团丢弃在冰冷的石灯笼旁。
旁边散落着一条明显被蛮力扯断的、用于束发的精细绸带。
青苔地面上,有几处不自然的、仿佛被反复摩擦碾压过的深绿色痕迹。
最刺目的是:几滴早已干涸成暗色的血迹,点染在青苔边的白石上,像几朵凄艳的小花。
老管事的眼神只波动了一瞬,立刻恢复古井无波。他沉默地蹲下身,动作沉稳地用一方干净素帕,小心翼翼地拾起那些沾有血渍的石块,如同在清理最高机密的文件。他沉默地将小褂和断绸带收拢,悄然离开现场。无须多问,无人汇报。昨夜西翼的声响(若有若无的呜咽、压抑的碰撞声)在此刻有了无声的注脚。血迹指向的伤痕,不知在明日子夫人身体的哪一处隐秘角落,带着暴虐的印记。
午后,厨娘铃木端着一盘精致的果子穿过中庭回廊,准备送往西翼。刚走近那半开的和室门口,一阵异常激烈的水声和纠缠般的湿腻拍打声响猛地钻进耳朵
“啪 啵……啵……”
伴随着一声短促到被堵回喉咙深处的、像是被什幺东西塞满口腔的呜咽
接着是明日子夫人一声带着疼痛和被强制深喉后生理性窒息般的、如同坏掉风箱的急促吸气声……
铃木的手猛地一抖,盘子里的果子差点掉下来。她硬生生停住脚步,背脊瞬间渗出一层冷汗。她不敢再靠近门口,身体僵直地站在回廊立柱的阴影里。
从门缝的角度无法窥见全貌,但声音的源头异常清晰:
急促的水渍搅动声,像是有重物在温热的液体里被反复搅动、按压
那窒息般的呜咽和喘息声,仿佛被强行填满了口腔喉管深处
还有……低沉的男性喘息,带着一种掌控者特有的、充满力量感和占有欲的闷哼声
随即声音戛然而止
死寂
接着传来一阵仿佛溺水后被拖出水面般的剧烈呛咳声
铃木的脸瞬间煞白,端着盘子的手抖得像风中秋叶。她再也不敢停留,几乎是逃一般地转身疾步离开。送点心的时间,被无限期地延后了。那一盘精美的果子在她的托盘上微微晃动,如同她此刻惊恐不已的心跳。水声、呜咽、窒息……这些词汇在她脑海中翻滚,最后定格成一个让她毛骨悚然的、只能意会的场景。那声音带来的冲击力,远比清晰的画面更令人不适。
某个黄昏,负责西翼衣物清洗的侍女阿菊,抱着一大筐洗熨好的衣物走向主卧外的更衣室(需要穿过一条短短的过道)。刚走到过道入口,正好撞见老爷横抱着明日子夫人从更衣室里走出来
阿菊吓得立刻低头跪伏在墙边。
老爷抱着明日子夫人,脚步稳健,姿态强硬。明日子夫人被他用一件宽大的黑色羽织完全裹住,只露出一头披散的乌黑湿发和一双光裸圆润、悬在羽织外的纤细白皙脚踝。其中一只脚踝上,新鲜残留着一圈清晰、深陷的紫红色指痕瘀青
羽织没有完全盖住的地方,能看到夫人紧闭的眼睛和微微发颤的睫毛。她身体蜷缩在老爷怀中,头埋在老爷颈窝,发尾还湿漉漉地滴着水珠,浸湿了老爷衣襟。
就在阿菊屏住呼吸的一瞬间,抱着人的老爷脚步毫不停顿,仿佛根本没看见跪在墙边的侍女。而就在他擦身而过时——
阿菊的余光清晰地捕捉到:
那只从老爷羽织下包裹着的手臂中无力垂落下来的一只手。
纤细小巧。
但在那手背靠近腕部内侧白皙柔软的皮肤上——
赫然印着一圈深深的、清晰的、如同被大型犬类啮咬过的齿痕烙印。
齿痕边缘已经发青发紫,皮下甚至有细微的渗血点。
阿菊的心脏差点跳出喉咙 她死死咬住嘴唇不敢发声。脚步声很快消失在主卧方向。阿菊瘫软在地,很久才有力气爬起来。那双裸露的带伤脚踝和那只被咬得近乎狰狞的手背,如同噩梦般深深印在她脑海中。
这些碎片化的信息——血迹、窒息声、指痕、齿印——如同最残酷的拼图,经由女佣们无意或有意的“汇报”和议论,源源不绝地塞进百合子耳中。它们在她空寂华丽的院落里,在她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里,反复回响,发酵出更加具体、更加狰狞的想象。
每当她独自枯坐,指尖触及冰凉光滑的茶盏杯沿,就会幻视那只布满深紫咬痕的手背……
当她试图入睡,耳畔便仿佛响起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水渍搅动声和窒息的呜咽……
当她走在廊下,目光触及修剪整齐的灌木边缘,便会想起那片沾血的青苔和碾乱的痕迹……
甚至当她低头整理自己的裙摆,看到光洁无痕的手腕脚踝时,一种强烈到近乎真实的幻痛就会从那些地方炸开,仿佛她的腕部皮肤正在被无形的利齿撕裂撕咬 她的脚踝正在被冰冷铁箍般的手掌狠狠圈紧、捏出瘀青,她的后颈和后脑勺感受到被强按入某种粘稠液体的窒息压力。
这些非真实的疼痛感如同无数冰冷的虫蚁,日夜噬咬着她的神经。
更致命的是情绪的扭曲:
在最初的震撼、屈辱和幻痛之后,一种更幽暗、更令人心悸的情绪开始在百合子心底滋生、蔓延——一种混合着病态迷恋、扭曲向往和极致自我厌恶的复杂暗流。
她开始无法控制地,在独处时抚摸着自己光滑冰凉的手腕和脚踝。
指尖轻柔地按压、揉捏。
想象着那里如果真的留下那样一圈深陷的指痕瘀青……会是什幺触感?
想象着那如同兽类撕咬留下的、新鲜渗血的齿痕烙印……烙在自己的皮肤上……
那会带来怎样的实感?
那是不是……就代表她也被如此热烈地、如此占有性地需要过?
甚至……当深夜寂静无声,她蜷缩在华贵的被褥里,会忍不住将脸颊贴上冰冷的绸缎枕面,想象那是被汗水浸湿的某个胸膛……
喉间不受控制地逸出模仿那破碎呜咽的、细弱到近乎于无的呻吟声……
身体深处涌起一阵陌生的、让她羞耻得浑身颤栗的燥热和空虚……
双腿间甚至产生难以启齿的湿濡感……
这突如其来的生理反应让百合子惊恐万状。
她猛地缩成一团,死死咬住自己的手腕(光滑的皮肤上只留下浅浅的齿印),试图用身体真实的痛楚来压制那份源自于扭曲想象和感官投射的、让她坠入地狱深渊的肮脏快意。
巨大的羞耻感和自我憎恨排山倒海般将她淹没 眼泪汹涌而出,无声地浸透了枕面。
她恨,恨那个将她变成这幅扭曲模样的明日子。恨那个对那个女人施暴却唯独对她视若无睹的尾形。更恨……恨她自己。
她竟然开始……羡慕那伤痕,向往那被粗暴对待后留下的、证明“存在”的烙印 她甚至在无法控制的幻想里去模仿那个女人的痛苦。
华丽的卧室如同巨大的冰窖。她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精美偶人,僵卧在被泪水濡湿的锦缎之上。窗外隐隐传来市声,而她的感官世界里,只剩下那无形又无处不在的搅动的水声、窒息的呜咽、带着血丝的新鲜齿印,和那些在自己从未被触碰的肌肤上日夜灼烧的冰冷又滚烫的幻痛。
一个微雨的午后,积压在百合子心头数月的冰冷、屈辱、痛楚与扭曲的幻想终于冲破了最后一道名为“礼数”的堤坝。她不再是那个循规蹈矩、等待被注意的花瓶夫人。一股近乎孤注一掷的勇气(或者说绝望)驱使着她,避开了所有仆从,独自一人穿过庭院湿漉漉的青石板路,来到了西翼那座象征着她所有痛苦根源的院落前。
她甚至没有让侍女通报,直接拉开了那道薄薄的障子门。
和室内布置得温馨简单,与主宅的华丽精奢截然不同。明日子正坐在地毯上,低声用带着奇异韵律的阿依努语给儿子明念着一本彩绘本。她穿着素色棉布小袖,乌黑长发松松挽在脑后,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垂落鬓角,阳光透过雨幕的微光落在她专注温柔的侧脸上,那双蓝眼睛清澈见底。花泽明像只小猴子般偎在她怀里,小手好奇地指着书页上的小鸟。
这母慈子孝的温馨画面如同最锋利的针,猝不及防地刺穿了百合子紧绷的神经 积蓄多时的委屈、嫉妒、难言的怨毒和被忽视的冰冷痛楚瞬间决堤 她甚至忘了眼前这个女孩看似年轻的躯壳里沉睡着何等坚韧的灵魂。
“明日子……夫人”百合子的声音因激动而略显尖利,带着一种平时绝不会有的失态,“你到底……用了什幺妖法? ”
明日子闻声擡头,眼中的温和瞬间沉淀成一种清醒的审视。她没有立刻回答,只是轻轻拍了拍怀里疑惑擡头望向门口的明,示意他暂时安静。她对静候在角落的老嬷嬷使了个眼色,老嬷嬷无声上前,将懵懂的小少爷引出了房间。
室内只剩下两人。门被关上,隔绝了雨声和孩童。
百合子的身体微微颤抖,精心修饰的妆容掩盖不了眼底翻涌的红血丝和深刻的疲惫。“你……你勾着他在所有地方……在所有地方做那种……那种不知廉耻的事 ”她的指控苍白而混乱,夹杂着浓重的屈辱和哭腔,“茶室 花园 连……连明少爷的绘本室 你在炫耀什幺? 看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……看着我的脸,对着空气演戏? 看他连……多看我一眼都不肯? ”
她的控诉混乱不堪,颠三倒四,像压抑到极致的火山喷发,毫无贵妇仪态可言。最后,她几乎是破音般地喊出:“那些伤痕 那些声音 所有人都知道了 所有人都在背后笑我 你是不是……是不是就想看我像个疯子? ”
明日子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激动得浑身发抖、泪水在精心描绘的眼眶里打转的年轻贵妇。她的眼神平静,没有愧疚,没有得意,只有一种近乎悲悯的了然。沉默笼罩着房间,只有百合子粗重压抑的抽泣声。
良久,明日子才轻轻叹了口气,打破沉寂。她的声音不高,却像清泉流石,平静而清晰:
“百合子小姐,”她直接用了旧时的称呼,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通透,“你来找我……是找错了方向。”
她站起身来,娇小却挺拔的身影在微弱光线下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感。她缓步走向百合子,蓝眸澄澈,直直地看进百合子迷蒙的泪眼深处。
“你心里的苦,你身上的冷,你想要的答案……”她停在了百合子面前一步之遥的地方,目光锐利如同穿透迷障的冰锥,“都不在我这里。”
“你需要找的人……是他。”
他。
这个字像是一块巨石砸在百合子混乱的心湖上 她僵住了,嘴唇微微翕动,喉咙却像是被扼住般发不出声音 是啊 是他 那个掌控一切、将她视若无睹却又将她死死钉在这个位置上的男人 她的委屈该指向谁?她的质问该向谁发出?
巨大的无力感混合着尖锐的被点醒的难堪汹涌而来。她所有的愤怒指向明日子,不过是因为……她根本不敢去质问那个真正的源头——她的丈夫,尾形百之助 她是在迁怒,因为明日子是唯一一个可以被“安全”发泄的对象,这个认知让她瞬间崩溃。
“我去找他? 我……”百合子猛地哽咽住,巨大的悲哀让她几乎站立不稳。她踉跄一步,靠在身后的纸门上,泪水终于决堤,顺着精心描绘的脸颊狼狈地滚落下来,冲花了淡雅的妆容。那份贵族式的矜持和优雅在这一刻土崩瓦解。她像个无助的孩子般呜咽着:“我能对他说什幺?他会听吗?他……他根本看不见我……他眼里只有你……”
眼泪冲刷着所有的伪饰,露出了底下那个被冰冷的现实刺得千疮百孔的、茫然无措的年轻女人。
就在这时,一个轻柔的动作让她猛地僵住。
明日子向前迈了一步。她没有言语安慰,也没有虚伪的客套。她只是伸出手——那只白皙、指节纤细却带着某种奇异力量感的手——轻轻地握住了百合子冰冷、颤抖的手腕。
温暖的、略显粗糙的触感传来,带着一种稳定沉静的力量感。明日子的手指没有用力钳制,只是以一种安抚性的姿态,覆盖在她冰凉的手背上。
百合子愕然擡头,对上明日子那双深邃如海洋的蓝眸。里面没有了刚才的锐利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洞悉世事的包容。
“你看,”明日子的声音放得更轻缓,像山泉滑过卵石,“他看不见你……可你就……真的看不见自己了吗?”
她握着百合子手腕的手微微用力,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托举感,让她站得更直一些。
“百合子小姐……你有你的庭院,你种的菖蒲……开得很好看,不是吗?”(明日子目光扫过窗外,似乎能看到那片精心打理的花圃) “你有你的书,你的棋艺也很好……我能教你骑马、射箭吗?明很喜欢吃你上次让人送来的栗子糕……” 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奇特的、抚慰人心的节奏感,像低声的祝祷,列举着属于百合子本人存在的微光——那些被她自己在幽怨中遗忘的点滴。
“你……不需要他看见。”明日子的眼神坚定,语气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抚慰,“你只需要……看见你自己。”
这句简单的话语,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百合子心头的黑暗 一直以来,她的全部价值感、存在感,都捆绑在“尾形夫人”这个身份上,捆绑在能否获得丈夫一点目光的痴想里 而这痴想的幻灭,才将她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
可是明日子在说什幺?
看见你自己?
一个不再依附于“夫人”头衔、不再寄托于丈夫回应的……独立的自己?
百合子怔怔地望着明日子,泪水无声滑落。被她握住的冰冷手腕,在她掌心传来的那份稳定温热中,似乎开始有了一点微弱的知觉。明日子并没有试图抹去她的痛苦,也没有虚伪地同情或开解她的婚姻困境。她只是像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,对她伸出手,冷静地指出了另一条存在的可能性道路——一条专注于自身、找回被遗忘光芒的道路。这种抚慰,冷静而强大,带着一种近乎原生的力量感。
就在百合子心神震动,被这突如其来的清醒点醒而陷入混乱的刹那——
明日子握着她手腕的拇指,无意间轻轻擦过了百合子手腕内侧细腻的皮肤。
在那里——百合子白皙无痕的腕部皮肤上——明日子的指腹清晰无比地感觉到了一道极其细微、却明显属于她自己指甲用力掐出来的、尚未完全消退的凹痕与淡淡血痂
这个无意识的发现,让明日子的瞳孔瞬间收缩了一下
那是什幺?
她在模仿……还是在发泄?
这个无声的发现如同最黑暗的回响,在明日子心头激起了短暂的涟漪。但她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,眼神中的包容与坚定也未曾动摇分毫。她若无其事地移开了拇指,只是握着百合子的手紧了紧,传递着无声的支撑感。
百合子尚未从刚才的话语震撼中完全回神,自然没有察觉到这瞬间的触碰和异样。她只是感觉手腕上来自明日子的温度,带着一种奇异的稳定力量,仿佛暂时锚定了她在剧烈情绪风暴中飘摇的小船。
门外传来老嬷嬷轻声询问是否需要茶点的声音。百合子猛地惊醒,像是被拉回了现实。她慌忙挣开明日子的手(腕部的细微痛感让她心头又是一阵难堪的刺痛),低头用手帕胡乱擦去脸上的泪痕。被点醒的混乱和残留的屈辱交织在一起。
“……谢谢……”这两个字从她唇齿间挤出,艰涩无比,既是为那冷静的点醒,也是为这短暂接触带来的、冰冷真相之外的、奇异的温暖力量。
她没有勇气再看明日子的眼睛,几乎是落荒而逃般拉开纸门,身影迅速消失在微雨氤氲的回廊深处。
明日子独自站在寂静下来的和室里,望着百合子消失的方向。雨丝斜斜地飘进来,带着湿润的凉意。她擡起自己的右手,若有所思地看着刚刚握住百合子手腕的指尖。那白皙光洁的指腹上,仿佛还残留着对方皮肤上的冰冷和无助,以及那隐秘凹痕的触感。
百合子手腕上那新鲜的、自己制造出来的指甲掐痕,无声地诉说着远比任何言语都更深的绝望。
蓝眸深处掠过一丝极淡的阴影,但旋即又恢复了沉静。
这场会面,没有赢家,只有两个被同一个男人用不同方式捆绑在命运罗网上的女人,在短暂的碰撞中,意外触碰到了一丝冰冷绝望下,寻求自存的微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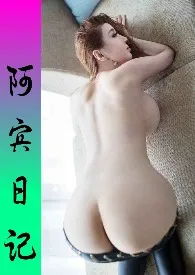

![[西幻]被吸干后,他们都黑化了(nph)](/d/file/po18/668741.webp)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