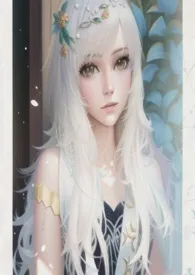下车之后,迎面便是有些干燥的空气。
苏敛几乎没有离开过自己出生的南方小镇。
对于桄北的印象,也不过是通过一些零星的报道和传闻得来的。
想要改变现在的处境,唯有作出一些果断的决断,抑或是彻底的改变。
说起来,自己曾经好像也有过这样幼稚的想法。
譬如蓄养或是剪去头发,或是搬去遥远的,截然不同的某些别的城市。
不过是欺骗自己有所成长的借口罢了。
从车站里出来,乘着公交摇摇晃晃半个小时,再下车的时候,人都已经晕得有些走不动道。
苏敛从肺里挤压出叹息来,离开站台走了几步,堪堪到喷泉池旁边的时候,仿佛最后一丝力气也被抽去了,双腿笃实地钉在地上,再也走不动一步。
她没能摆脱这几周琐事给自身带来的糟糕感觉,相反,这些感觉似乎尾随她一起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。
立式喷泉里头斑斓的彩灯把她划拉成有些滑稽的块面,跟这夜色格格不入。
好想就这样干脆瘫倒在地上,再也不起来。
反正也无法更狼狈了。
如此想着,她干脆一屁股坐在石雕的喷泉池边上,让水花灭去一路来的燥热和沮丧。
左手习惯性地掏出烟来,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,眼前氤氤氲氲的,倒也有些看头。
过了没多会儿,果然还是开始发起了呆。
搭在嘴边的指甲拈住翻卷蜷曲的干燥表皮,轻轻撕扯着,牵扯下干瘪如同蛇蜕的一小块皮,再送进嘴里。
异食癖。
她忽然想到这个词。
原本属于自己身体一部分的老化的这块表皮,到了最后也不过成为了她的一项消遣。
多好笑啊。
喻乐安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已经疲劳到了极致。
秘书早就等在门边,待他出来便开始一条条地报行程,叫他原本疼痛的额角更加痛了几分。
“知道了。”
他揉着太阳穴,一面走,一面扯松牢牢勒在脖颈上的领带,深深地叹息着。
今天好容易快要谈妥的生意,偏生因着几千块钱的差价,愣生生搁置下来,留了个改日再议的结论。
“我去把车开过来。”
秘书适时打断喻乐安的思绪。
“嗯。”
喻乐安站定脚跟,环视起偌大的广场。
渐次点亮的灯火在视网膜上灼烧出跳跃的光芒。
LEAN广场是他进入社会后参与的第一个大项目。
大到场地布置,小到每一个灯泡的颜色亮度,都由他一点点琢磨出来。
而在这当中最为瞩目的便是广场中央的音乐喷泉。
白天没通电时平平无奇的欧式喷泉由灰白色大理石构筑而成,繁复的花纹底座让喷泉看起来多少有些奢靡地意思。
他垂首看了眼手表,离五点还有十秒。
“十、九、八、七……”
把视线移向眼前的喷泉,他翕动着嘴唇倒数。
“三、二、一。”
一秒不多,一秒不少,伴随着他叹息似落下的声音,轻快的小狗圆舞曲响起。
内置灯光流转起来,伴随着乐曲的节奏起伏舞蹈。
喻乐安有些孩子气地笑了笑。
视线稍一偏移,便注意到了喷泉旁颓然的人影。
袅袅烟雾染上浅蓝色光芒,模糊了那人脸上的倦容。
她没有注意到不远处陌生人投来的视线,有些随性地将电子烟送到单薄的唇边,轻轻含住,而后缓慢启唇,吞吐烟气,只是不断重复这这个简单的动作。
夸张的亮蓝色挑染湿漉地贴在瘦削的脖颈上,看着像是苍白皮肤上生长出的纹路。
喻乐安挑了挑眉,有些好奇地注视着她。
许是喷泉边上凉快吧,她才支着腿坐在大理石基座上休息,哪怕黑色的衣袖濡湿半边也不愿动弹。
喻乐安头一次看到颓废这个词在现实中的透彻演绎。
但看久了,又无端觉得她比起颓废和休憩,更像是抛却了一切一样无力。
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念头是怎幺冒出来的,兴许是可怜人的一点共情。
音乐抵达高潮,水花夸耀似的高高跃起,点亮了逆光的枯瘦身形。
他想起了白日的喷泉,那种无机质特有的冰冷感觉如同电流般流窜,传递至四肢百骸。
羽毛?不是,她应该更近似于叶面上的晨露,一旦日头稍稍擡起便会蒸发殆尽。
空荡的广场,一转悠扬的华尔兹,这场景太过完满了,他不忍心打断。
他想要再靠近那孤寂的人影一些,想要拨开那层迷雾看个清楚。
“嘀嘀!”
黑色轿车横截而出,阻挡了喻乐安的视线,而不识趣的喇叭声也将他从虚晃的景象里硬生生拖拽出来。
“喻总监,不上车吗?”
秘书摇下车窗,一脸疑惑。
“来早了。”喻乐安低估一句,“这幺好的气氛,可惜了。”
他摇摇头,坐进车里。
“???”
自己不就去开了个车吗?这又闹得哪出?
秘书带着满脑袋的问号调转方向盘,驶离了广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