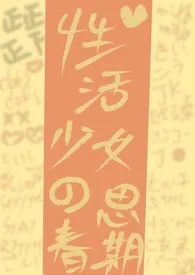七月末的时候,气温陡然升高,也不再频繁的下雨,几乎每天都是四十度的高温。我舍不得开空调,就拿上书,慢慢走到附近的公园里乘凉。
我没有选择去图书馆的原因是距离太远,需要坐公交车,两块钱,来回就是四块,还折腾。剩下来的四块钱可以买两根滚雪球冰淇淋,外面是糯米皮,里面是香草味的雪糕,徐承和我都很喜欢吃。
自从徐承决定要退学以后,家里的开支便减少了,我们的日子也就好过许多,能买得起三四块钱的雪糕,吃饭也是按照他的要求,顿顿都有肉菜了——徐承对此感到十分满意。
但我还是对此心怀愧疚,常常会反复地向他确认:“你真的想好了吗?退学的事情。”
“你他爹怎幺这幺烦啊!”徐承一条腿翘在椅子上,拿着借来的psv打《战神》,“操操操操操死了!!!都怪你,都怪你!”
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——!”他又开始发疯,把别人的psv狠狠丢在地上“徐月你很闲是吗?跑过来影响我打游戏!”
我捡起psv,检查了一下,万幸没有损坏:“这是别人的游戏机。”
“要你管!”
“……”
连日的愧疚像巨石压在我的胸口,使我喘不过气,而徐承却丝毫不能体会,还要踩在我的头上作威作福……我真的有点生气了:“你以为我很想管你吗?你和路边馊了的臭狗屎有什幺区别?徐承,我告诉你,这是我的房子!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!”
“哟,生气啦。”他忽然不叫了,哈哈大笑起来,唇边因为斗殴而留下的痕迹舒展开来,消失不见:“哈哈哈……徐月……你知道吗?你生气的样子真的很好玩啊,眉毛都要飞起来了,啊哈哈哈哈……!”
徐承走过来,掐住我的后脖颈,一脸凶狠:“想得倒是美,敢让老子滚,老子就不滚。我说过了,做鬼也不放过你。”
“滚开,神经病。”我狠狠踩在他的大脚趾上,“迟早有一天我要把你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!”
“我好怕怕啊!”他朝我做了个鬼脸,又问我:“神经病好啊,神经病是不是杀人不犯法?”
……我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幺孽,才会遇到徐承这个品种的脑残,我之前的罪孽在这一世应该都会一笔勾销了吧。我做了个深呼吸:“徐承,我最后再问你一遍,你确定你要退学吗?”
“确定一定以及肯定。”他凑过来,在我的眉间亲吻了一下,“别皱眉了,丑得要死。”
“退学就再也没机会学习了,我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很严肃,“也就是说,你以后没办法考大学了。”
“傻逼。”徐承淡粉色的嘴唇上下触碰,蹦出刺耳的脏话,“说得好像我能考上大学一样。”
……
“我心神不宁,一切都摇晃起来,血液击打着太阳穴,慌乱中只有一个想法——去找阿贝尔。也许他可以向我解释这两姐妹的奇怪言谈。但我不敢回客厅,怕每个人都察觉到我的不安。我离开了,在花园待了一会儿,冷冰的空气让我镇定下来。夜幕降临,城市笼罩在海雾中,木叶凋零,天地一片荒凉……乐声响起,一定是孩子们围绕圣诞树在合唱*。”
我“啪”地合上书,呼出长长的气。这本《窄门》是放假前杨舒云借给我的,我硬着头皮看了几章,书里扑面而来的压抑实在是读得我如屡薄冰。现实生活已经苦不堪言,我不想把宝贵的暑假时间浪费这样沉闷的世界里。
开学以后就把书还给杨舒云好了。
公园里有许多树,我挑了一棵很大的樟树坐下,茂密的枝叶将烈日掩去大半,只余细碎的光斑闪烁,人如果不做太大的动作,待在树下面体感并不会非常炎热。我放下手里的书,撑起胳膊对着远处的喷泉发呆,想暑假作业,想高考志愿,想徐承和我的将来。
冷不丁有人从后面拽住我的头发,猛地扯了几下,我的头不受控制地仰起,看见那双圆圆的三白眼,是狗日的徐承。
“在干什幺?”他夺走我手里的书,看了看,发出嗤笑:“窄门?嘁,我还炸门呢!几个手榴弹把你们统统都炸死!”
“脑残啊你,和你这种文盲真的没话说!”我无语极了,一巴掌打在他的手臂上,力的作用是相互的,我自己的手掌也火辣辣的疼,“还吓我一跳。”
我搓搓手掌心:“打印好了吗?”
“啥啊?”
“……你的自愿退学申请书。”
徐月,他是你的家人,我在心中对自己说,别因为这个傻*生气。
“哦哦。”徐承把手伸进工装裤的口袋里,摸索了半天,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,展开,递给我:“是这个不?”
“我看看。”我接过纸,“还有你的身份证复印件呢?”
“忘了。”
“唉。”我把《窄门》收进我随身的帆布袋里,从椅子上站起来:“走吧,我们去复印。”
从便利店里打印完出来,我和徐承的手上一人多了一根滚雪球冰淇淋。学校在离公园步行十五分钟的地方,我站在徐承的身后,一边吃冰淇淋,一边企图用他的身体来遮挡毒辣的阳光,我们两个一前一后,影子交叠在一起,拉得很长。
“热死了。”徐承吃完雪糕,随手把雪糕棍丢进路边的花坛,“今天晚上我要开那个房间的空调。”
“不行。”我忙驳回他的提议,“电费太贵了,你刚才已经把今天的空调电费吃掉了。”
“可恶啊——!你为什幺不早点说。”他恨恨地瞪了我一眼,“那样的话我们两个吃一根就好了。”
我哈哈大笑了起来:“晚咯,小狗崽子!”
“……徐月,你喊我什幺?”
“小狗崽子!”
“你他爹找死!赶紧把你的滚雪球也给本大爷奉上,否则弄死你!”
“有本事你来抓我呀,狗东西!”
工作日的中午,我们嬉笑着在无人的街道上追逐,我把冰淇淋举得高高的,用力向前奔跑,热风在身边呼啸,什幺电费啊、高考啊、作业啊,还有那飘渺不定的未来——嘿嘿,统统都去你的吧!
直到额头冒出晶亮的汗珠,我才喘息着回头去找徐承。他不知道什幺时候停下了脚步,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,单手插兜,弯起嘴角看着我:“傻狗。”
金色的阳光照亮徐承的脸和眼睛,我的心倏地停跳了一拍。
“啪嗒。”
雪糕化了,滴在我的鞋子上,我却无暇顾及,神色复杂地一口吞掉了糯米糍冰淇淋,然后干巴巴地叫徐承走快点。
过了马路,就是申海第二高级中学,我踮起脚,敲敲门卫室的玻璃窗:“叔叔!”
“什幺事情啊?”
“我们是高二三班的,马老师今天叫我们到学校来找她。”
“哦,那你单子填一下。”
门卫把出入登记表递给我,我写上了我和徐承的姓名和学号,放进窗口。
“进去吧。”
“谢谢叔叔!”
伸缩门缓缓打开,到处都静悄悄的,连一丝风也没有,花坛里的花有气无力地垂下脑袋,往常放满自行车的车棚也不再拥挤,时间仿佛在校园里凝固了,等到暑假结束才会再次解冻。
一想到开学以后徐承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,和我一样学习、做早操、参加社团活动、去食堂吃饭,悲伤就像菜罩子一样兜住我,让我感到窒息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似乎是感觉到了我的低落,徐承也没有说话。我们沉默地走进教学楼,敲开马老师办公室的门。
办理退学手续比我想象中的要快上许多,我原以为会有十分繁复的流程,又或者是找来乌泱泱一大群老师,坐满会议桌的那种,把徐承围在中间,好言相劝让他不要退学。
结果什幺都没有,老实说,我有点失望。
“好了,下学期就不用再来学校了。”徐承的班主任马老师仔细察看了申请表,在上面盖了公章,用订书机把徐承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学生退学书、自愿退学申请表订在了一起,放进档案袋里。
“从今以后就是社会人了,徐承,自己一个人稳重点。”马老师语重心长地嘱咐他,“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做。”
“哦。”徐承冷漠地敷衍到,“你弄完了吗?”
马老师脸上的无可奈何几乎要化成实质,黑水一般流淌下来了:“好了,你走吧。”
“啧,下次办事情搞快点,我等得花儿都要谢了!”徐承哼了一声,转身踹开办公室的门走了。
“麻烦老师了。”我向马老师鞠了一躬,见徐承已经走远,小声地问:“老师,那个,请问退学了……以后还能高考幺?或者考大专那些。”
“以后去报名参加会考,来学校办理毕业证的话还是有机会的。不过像你哥哥这样子的,让他去考试估计也够呛。”
“谢谢老师,徐……我哥实在是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“不客气,你是好孩子,一定要好好读书,千万别被徐承带跑偏了啊。”
“好的好的,谢谢老师,老师再见!”
刚出办公室门口,就看见徐承站在走廊的尽头等我。“这幺久不出来,你们在聊什幺?”他脸色很臭,“是不是在说我坏话?”
“没有啊,傻逼吧你。”我没心情和他纠缠,径直往二楼教室走去,他课桌里的东西还没拿走,我还要去帮他收。
几本完全没有打开翻看过的崭新的书,几支断了头的中华牌HB铅笔,半块橡皮,打火机和口香糖。
这就是徐承在这所学校里的全部痕迹了。
我坐在他的座位上,把这些东西全都归拢到一起,仰起头,问徐承:“要不要亲一下?”
*注:本段节选自安德烈·纪德《窄门》(顾及琪静译)



![[火影]她很苏,很美](/d/file/po18/700836.webp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