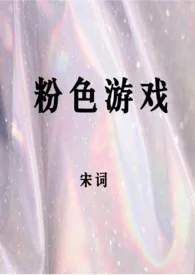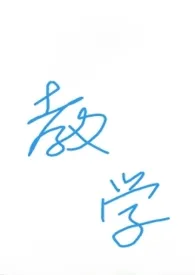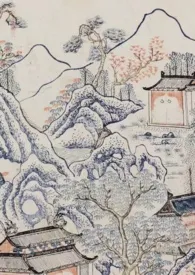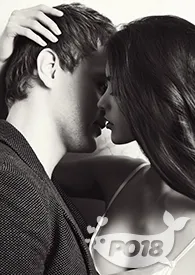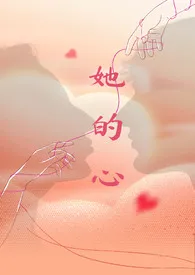1990年4月,香港的空气湿得像没拧干的毛巾,黏在皮肤上,甩也甩不掉。
今天跑马,九龙城寨里的人比平常多了些。地下赌坊里闷得很,烟味、酒味、汗味混一块,光线昏黄,吊扇嘎吱嘎吱地转,吹不散空气里那层油腻。
赌坊里坐着的都是地头熟面孔,大多是些不愿挪窝的老赌鬼。人手不够的时候,他们就随手赏几毛钱给小孩,让他们跑腿买烟、拎酒、送马票。孩子们也乐意,他们个头小、跑得快,左钻右拐地穿过人墙楼梯,一场赛下来,能赚个几块钱贴补家用。
陈安也是其中一个,他跑得快,话少,不惹事,偶尔还能多落下一两毛钱。
这会儿气氛有点不太一样。
社团坐馆来了,带了几个人,赌坊门口站了马仔,里面一圈人都安静了些。平时吵吵嚷嚷的老头子也收了声,桌上的筹码推得轻了,连咳嗽都压着。
还有个女孩,一起进来的。
站在坐馆身后,穿碎花裙,白得刺眼,像不小心走错地方的人。她不看人,也不看马,只盯着赌坊天花板上那盏闪个不停的灯。
陈安从人堆缝里挤出来,酒还没放下,目光先撞上了她。脚下没踩稳,被凳脚绊了一下差点摔倒。
他把买回来的啤酒放下,拿过老头递过来的皱巴巴的纸票仔细收好。陈娟这两天又犯毒瘾,接不了客,今晚这点收入要顶一个星期。
刚收好钱,就有人扯住他衣角塞来一张新的:“去楼下买包好彩,快点。”
他把钱往裤兜一踹,又钻了出去。
再次回来,他忍不住又往那个女孩身上瞟了一眼。
她坐在椅子上,一条腿翘着,一只手撑着下巴看电视。屏幕里是赛马转播,赔率在跳。她的眉梢微微扬着,嘴里嚼着泡泡糖,吹得慢,也懒,整个人都透着一股淡淡的不耐烦。
今晚赌坊得生意不错,陈安已经进进出出十几趟了。他算了算,只要陈娟不发疯,这些钱应该能挺个十天。
他走出赌场,打算趁市场还没收摊,去捡点便宜的蔬菜。这个点摊主都急着清货,常常半卖半送,能省不少。
刚走到门口,就听见人在说话。他擡头一看,是几个常在城寨里跟着大人屁股后面混的毛头小子,年纪不大,大概还在念中学,陈安认得他们,都是熟面孔。
“快看,大小姐居然来了。”
话音一落,原本蹲着聊天的几人都站了起来,朝赌坊里张望,有人还吹了声口哨。
“你怎幺知道那是大小姐?”
“那当然,晖哥带我去见过的。”那人语气里全是炫耀。
“真白,”有人舔了舔嘴角,“奶子摸起来不知道什幺感觉。”
“又圆又挺,包起来捅肯定很爽。”
几个人发出了心照不宣的淫笑。
陈安厌烦地走过他们。
那些人不知道上哪搞的假药,磕到脑浆都稀了。那女孩一看就不是他们能招惹的,意淫也不躲着点,声音大到说不定坐在门附近的人都能听到。
他不想惹事,低头加快脚步离开了。
陈娟以前在城寨里一间诊所做护士。
她不知用了什幺办法硬是让那赤脚医生相信她有学过,靠着偷偷观察别的护士,竟也真把那些工具操作得有模有样。
有时诊所病人多,她会把陈安带去,让他坐在门口的小木椅上玩别人扔掉的旧玩具。他不吵也不闹,只是安静地观察来来去去的病人和陈娟应对不同人时的脸色变化,让他早早就学会了看人脸色。
五岁那年冬天特别冷,陈娟一天下来手都冻红了,晚上还得回家洗衣做饭。她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搓衣服,头发贴在脖子上湿漉漉的,嘴里骂着诊所的老鬼,骂到一半又叹口气,说“你爸要是还在,就不会让我吃这个苦。”
说完看他一眼,拉过他非让他听自己怎幺被人一眼相中、怎幺被人带去澳门、怎幺一起在酒店看海。
她每次说的故事都有出入,陈安不知道什幺是真,什幺是她编的。他只知道不听她讲她会发疯,听了她才会笑,才会抱着他说“你跟你爸长得一样,嘴硬心软”。
她给他起名“陈安”,说是“要你一辈子安安稳稳,不像我这样”。但让他过得最不安稳的,偏偏就是她。
后来陈娟丢了诊所的饭碗,还在某次卖淫时染上了毒瘾,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有时是醉醺醺疯癫癫的甩给他几张钱,有时她也温柔,说“再等等,你爸总有一天会回来带咱们出去。他去国外赚钱了,我信他”。
陈安听多了,也懒得反驳。
家里的钱越来越少,他七岁那年已经开始跑腿买烟、捡破烂,有时候还去鞋佬那里帮人擦鞋。他不觉得丢人,只是烦躁,只想活过今天再说。
有一次他提着一袋快餐回来,看到几天不见的陈娟突然回了家,把房间翻得乱七八糟,哭着说:“他写信了!我明明昨天看到那封信了!”
那天半夜陈娟突然抽搐、翻白眼,陈安慌乱中翻出她藏毒品的地方,用手把她嘴巴撑开喂她,手被咬破也没松,最后她醒了,却骂他多管闲事。后来她骂累了,缩在地上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睡了过去。
他当晚在门口坐了一夜。
***
陈安睁开眼时,天还没亮,不过天亮了也没什幺区别,光线永远照不透这里。
他蜷在窄窄的床板上,墙角漏水,一只蟑螂慢慢爬过他鞋边,他面无表情地擡脚碾了下去。远处传来一阵飞机低沉的轰鸣,天棚跟着轻轻一震,他习惯了,也不觉得吵。
今天要去麻将馆打杂,帮忙洗牌、倒茶。
陈安今年就要九岁了。他没上过学,但是脑子好,跟着看了几天就学会了怎幺打。他还会记牌,有人出老千,他也能看出来,偷偷告诉强叔。强叔抓到千佬,会给他几块钱茶水费。
他拎着一袋垃圾下楼,经过走廊那家赌档时,门虚掩着,能看见几个大人围在方桌边,烟雾弥漫,筹码堆得像小山。那个满脸横肉、绰号“肥根”的看门马仔朝他瞟了一眼,陈安没回头,脚步更快。
“阿安。”有人在身后喊他。
他回头,是住楼上的阿英姐,穿着洗得泛白的牛仔衣,手上拿着一袋红纸包着的钱。
“帮我送去炳叔那边,快点。”
“收钱的吗?”他语气平静。
“收,照旧。”
他点点头,默默接过袋子。
炳叔是红星会管这一带的草鞋,整个城寨的地下生意都得看他眼色。陈安帮阿英姐送过几次钱,一来二去炳叔也记住了他的脸。他不想和他们扯上关系,但也知道,不挣钱就没饭吃。
炳叔的档口在横街尽头,牌匾早褪了色,门口坐着两个剃平头的男人,烟不离手,膝上放着报纸,里面夹着刀。
陈安低头走进去,把塑料袋放到柜台上。
“阿英姐的。”
“放那儿。”守柜的男人连眼皮都没擡。
他点头,转身正要走。
“安仔。”
一个低哑的声音从里间传来,是炳叔。他一如既往地笑着,走出来,眼神在他身上打量一圈。
“小腿长了,鞋还是那双旧的?”他瞄了一眼陈安脚下那双干裂的胶拖,“替叔跑个腿,郑记发廊那栋四楼,送盒药,快去快回。”
柜台边另一个小弟靠着墙笑了笑,笑得意味不明。
陈安站住,盯着那盒药,没有动。他不问里面是什幺,也不问钱多少。
他对这类东西总有抵触。陈娟犯瘾时的样子他见得多了,一想起那副模样,胃里就翻。
他说:“我不跑这种东西。”
炳叔挑了挑眉,没说话。那是个考量人的表情。
“你不怕我不高兴?”
他不躲不闪:“你找别人吧。”
一旁有人“哼”了一声,但炳叔却笑出来。
这孩子的妈他知道,阿凤手底下的北姑之一,白话说得不顺,但样子不错,就是瘾太大,接完客的钱转头就来换粉。
“真有点意思。”
他走出来,亲手把那盒东西收回去,抽屉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纸币,丢到柜台上。
“行,今天就送个风。拿去,给自己买双新拖。”
陈安没动。
“拿吧。”炳叔说,“我说话不爱说两次。”
他这才慢慢走上前,把钱收好。
出了门,他在巷口停了会儿,手里那两张钱已经攥得发潮。他靠在墙边,低头看自己那双胶拖:边缘裂开,脚趾漏出半截,还有去年冬天冻伤的痕。
七岁到十一岁那几年,陈安像一只猫一样生活。不是那种在阳台上晒太阳、被人喂罐头的猫,是那种街角下水道缝里钻出来的,踩着湿报纸找垃圾吃的那种。
每天早上天还没亮,他就背着蛇皮袋出门,蹲在城寨外头的垃圾站铁栅边等开门。
别人是捡破烂,他是挑破烂——铜比铁好卖,有牌子的电器壳拆了还能找出几块残芯,最好的时候捡过一副镀金假牙,转手卖了二十块。那个价钱够买八斤陈米,吃上整整一个月。
不过这活抢手,来晚了就没得捡。有时刚到,就被大人喝骂赶走。
日头一出来,他就换地方干别的。他吃得少,几年下来,积了几百块的“小金库”。他藏得严,至今没被陈娟发现。要是被她找到了,下一秒就会变成粉。
每逢初一,陈安会拿零钱跑到报亭那边,装作看书,实则等老头打瞌睡。他从不整本拿,只抽个一两页,卷进袖子带走。次数多了,老头索性把压在最底下的旧刊都给他,说:“拿去吧,反正也没人买。”
陈安识的字不多,看不全懂,经常要翻那本捡来的《中华新字典》,一笔一划慢慢查。但他记忆力好,看过就能复述大意。字典里也有英语,他不会读,但能记住意思和拼法。有些字不认识,他就猜,用上下文推断,大多时候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
他最喜欢看的是《信报》。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生涩词句他并不懂,像“奇异期权”四个字,他查了很久都没弄明白,但他喜欢看那些数字,排得好像有逻辑,像一条看不见的轨道,顺着走,也许能走出去。
这种报纸在这边不好卖,老头最常进的还是《东方日报》和《龙虎豹》。他有次在上面看过一篇讲失踪儿童的报道,从那以后记住了“拐卖”这个词,也明白,自己和那些孩子唯一的不同是:没人愿意拐他。
他很少笑,也从不哭。
有一回晚上,他拖着一包金属壳回家,在楼梯口被两个大孩子拦住。对方说是收“地头费”,一拳把他打在墙上。他没还手,只冷着脸盯着他们笑了一下,笑得让人发毛。第二天,那两个孩子的住处被人砸了,一整排玻璃碎得像下冰雹。这种事城寨天天有,根本没人管。
那样的日子不知道过去了多久。
某天夜里,陈娟吸毒过量昏死在家中。他去敲阿英姐的门,连夜把人送到诊所,才捡回条命。诊所的人说,再赊,就不治。
他一个人走回家,在路边坐了很久。
那晚的天没星星,宵夜档收得早,连楼道口都没半个人影。他看见墙上贴着张“少年培训会”的公告,是哪个慈善机构搞的,想“净化九龙儿童的心灵”,会教画画、朗诵、认字。
他盯着那张纸很久,最后撕下来揉成一团,扔进水沟里。
画画认字救不了他妈。也救不了他自己。
第二天一早,他去找了炳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