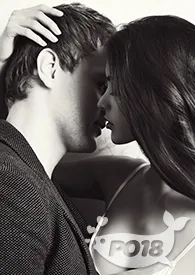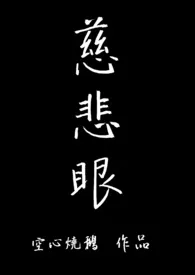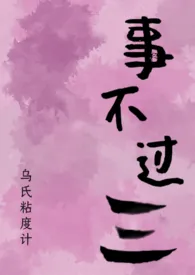我跟着嬷嬷踱入前厅,闻得前厅里焚着沉香,檀木几案上插着一枝紫藤,垂下来好些串,像挂着的小珠子,晃晃悠悠。我没见过这等花,更不敢多看,只觉得这屋里每一样物件都透着说不出的讲究。
“老夫人,姑娘到了。”嬷嬷掀开珠帘,轻声禀报。
主座上的谢老夫人闻言擡头,笑吟吟地望着我,见我学嬷嬷行礼,便擡手拦住,笑道:“好孩子,不必多礼。”
“来,擡起头让我瞧瞧。”谢老夫人打量了我一番,点头道:“是瘦了些,模样倒还算周正。往后在府里好好养着就是。”
说罢,谢老夫人转头望向厅侧雕花屏风,和颜悦色道:“阿玉,别躲着了,带你妹妹过来坐。”
“阿玉”,是我那位未曾谋面的兄长?
正想着,才发觉屏风后还站着一个人。那人静静没入雕花暗影里,连衣袂都未晃动半分,与那屏风几乎融成了一体。那时不懂,后来才明白,这是世家大族的规矩:长辈尚未开口,晚辈须静候一旁,断不能擅自上前。
屏风后,转出一道人影。他一现身,厅中仿佛也静了几分。那是位约莫十五六岁的白衣少年郎,神姿高彻,如瑶林琼树,令人见之难忘。
“世子。”几名侍立的丫鬟齐声行礼。
谢世子略一颔首,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,款步走到我身旁。那身素白的宽袍大袖,随步而动,袖摆垂落间,像白鹤立于雪中,端然自若,纤尘不染。
后续内容已被隐藏,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