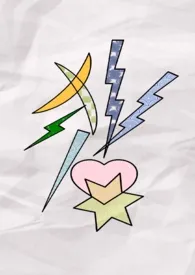时间|2050年 9月中旬
地点|麻省理工学院(MIT),计算基因与合成生殖工程系
波士顿的秋天总是带着一点剔透的凉意。校园中枯黄与深红交错的树叶被风吹得轻轻翻起,像是翻阅着一页页未完成的学术草稿。岭翔坐在MIT主图书馆的阅览桌前,手中拿着一杯已冷却的黑咖啡,眼神却还停留在不久前收到的那封电子邮件上。
「Congratulations, your paper has been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Genetic Computation and Reproductive Systems journal.」
这篇关于Y染色体微型序列变异与神经调节机制之间关联的文章,是他花了两个月才完成的初步研究。虽然还只是系上协助学生发表的学生版期刊,但主编在审稿信中的评语却异常肯定:「精确、独立、极具潜力——若持续深究,有可能延伸出崭新的生殖工程模型。」
教授在课堂上也当众点名赞许他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设计,甚至主动询问他是否考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
而岭翔只是轻声应了一句:「还早。」
他的眼神却不自觉地望向窗外,某个更遥远、更模糊的方向。
图书馆外的草地上,几位学生坐在长椅与石阶上讨论作业,笑声时而从风中飘过来,但岭翔并未加入。他一手拎著书包,沿着校园东侧的人工湖边慢慢走着,湖面倒映着一栋栋玻璃帷幕大楼,像另一个静默的世界。
经过基工系实验中心时,有位女学生从自动门口出来,认出他,朝他点头微笑。他也点了点头,步伐未停。
后续内容已被隐藏,请升级VIP会员后继续阅读。